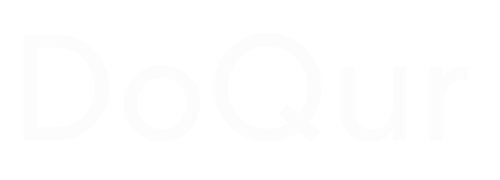整部親情賀歲片,幫你找回喪失的年味
而去年的《年年有余之鱼灯》,落點同樣在情懷。
看似直觀的魚燈,只不過製作起來有著很多門道。
《棒!少年》的成功,一方面在於它擁有不輸喜劇片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也涵蓋了對中國當下社會中存有的社會階層差別、留守兒童教育等等社會議題的檢視與關注;
只不過早在《棒!少年》之後,許慧晶已經在記錄片應用領域斷斷續續摸爬滾打了十多年,也攝製過許多歷史紀錄經典作品。
就連幾歲的小孩子,課餘也會在老師傅的指導下幫忙製作魚燈,滿臉認真地用膠布固定住魚燈的骨架。
而他的最新經典作品《年年有余之鱼灯》也同樣如此。
大學堂裡傳來朗朗讀書聲,“小河彎彎出青山,大河彎彎流向海”,稚嫩的童聲在古老的徽式建築物中傳蕩反響,碰撞出一種超越當下時間的新老交融。
這是支帶有公益慈善性質的隊伍,隊員全數是來自全省各地的貧窮幼兒。對於那些10歲左右的小孩而言,籃球是掙脫身世的惟一出路。而每一次勤奮體能訓練與用力揮棒中,都是自己對宿命的叫板。
我們一邊緬懷著過去,但同時也在選擇性地遺忘和捨棄:
某種意義上,許慧晶的每次創作,都是對“來處”的一次探索。
在某種程度上,它更是現代人對未來始終報以幸福希望的意志。
但身為外來者的許慧晶,依然延續了他一貫的文化情懷,在非常有限的時間裡用攝影機捕捉到汪滿田村平靜、真實、幸福,並能同每一名觀眾們實現感情交互作用的細小日常:
而這,也是支付寶和許慧晶編劇去往汪滿田村,記錄魚燈會的初衷吧。
我們之後提及過,魚燈代表平民百姓對新兩年的期盼與祝願。
更難得的是,許慧晶對那個村子的探索並沒有逗留在目之所及的表面,而更深入發掘隱藏在景貌與民風背後、與魚燈有關的人文延承與感情傳遞。
編劇許慧晶憑藉著整部電影被更多人認識到,成為最具發展潛力的記錄片製作者之一。
那是我們的來處,也許,也將指引我們未來的去路。
許慧晶在向外關注的同時,也在創作中不斷向內發掘、探索自我。
電影最初在2020FIRST電影節現身時,就被視作“FIRST最強大黑馬”,並最終贏得了最佳歷史紀錄長片獎。而在公映後獲得這種的戰績,也並不讓人深感不幸。
每年新年,汪滿田村都會舉行一年一度的舞魚燈慶典活動典禮。
追隨螞蟻僱員靈草的視角,影片在今年春節之後來到了汪滿田村。
舞魚燈有如集體共同參予的禱告,充滿著每家每戶對來年生活的幸福願景。
少於4.8萬豆友,共同為整部影片打出了8.7的高分,四星五星的打分佔有了其中絕大多數。
而年長現代人参予魚燈會的準備,則是向自身“來處”的探望。
喪人文的流行,年味的遠去,一定程度在於現代人對現實生活的過分關注與讓步,進而遺失了曾經對生活最簡單、真摯、炙熱的期盼。
檢視並展現出不熟識的事物,難免會陷於獵奇的雷區。較之跟拍十多年的記錄片,《年年有余之鱼灯》整部只有短短的6分多鐘的賀歲歷史紀錄影片,在創作過程中似乎不具備充份觀察並融入被歷史紀錄者生活的時間。
又有多長時間,沒有真誠為聖誕節的來臨而喝彩與驚訝了?
但,魚燈誕生的600年來,代代相傳的不止民俗文化傳統與技藝,還有一套積極主動悲觀的生活價值觀念。
此項從清朝開始延承了600十多年的年俗典禮,現如今已經成為歙縣非物質自然遺產生態環境的活化石。影片就記錄了身為非遺人文傳承人的汪在郎準備2021年新年魚燈會的過程。
它關注到曾做為新年主流卻慢慢退隱至邊緣的年俗人文,讓現代人重新看見並繼續傳承從前這些幸福的存有。
他從一開始,就表達出對與時代密切相關的社會議題的興趣,通過《河岸》和《妈妈的村庄》三部前期經典作品,希望為相同族群、相同社會階層的觀眾們提供更多溝通交流的窗口,“提供更多一個互相認識、互相理解、相互寬容的媒介”。
魚燈會此項年俗典禮,對於生活在當地的老百姓而言,就意味著一種人文上的“來處”。
但是那些典禮,恰恰構成了我們對新年年味最初的記憶。
回顧2020年,院線上映的國產片中擁有豆瓣最低打分的,是許慧晶編劇創作的記錄片《棒!少年》。
這是編劇為支付寶攝製的一部賀歲發展史紀錄影片,故事情節聚焦的是江蘇徽州地區擁有少於六百年發展史的傳統年俗——魚燈。
2019年的《七里地》聯合許鞍華編劇,講訴了祖孫三代人的故事情節,通過一個直觀的“福”字,串連起鄉愁情緒;
所謂“來處”,是宿命與人文的根基,它在一定程度上刻畫了一個人的個性、價值觀與感情。
另一方面,它真實且頗具人物關愛的筆法,與觀賞者形成了感情上的共鳴與聯結,讓現代人的情緒隨著攝影機中被歷史紀錄者的宿命上下起伏。
老人家和小學生一同,在空間非常有限的迴廊裡舞動著魚燈,像是要把歡樂與祝福傳遞給在場的每一個人。
魚燈會是一項集體性質的公益活動,不但須要每家人的募款,同時也須要自己身體力行的幫忙。
此種意志與熱誠,正好是當代人在快節奏的都市生活中漸漸缺失與遺忘的。
老、中、少四代宗祖家人彙集在宗祠庭院,一邊笑著閒聊,一邊報名為將要開啟的魚燈會做準備。
希望現代人能從這堅持了600十多年的年俗傳承中,重拾對小時候聖誕節的記憶與期盼,也重拾對中國傳統年俗人文的重視。
而兒時陪伴著我們的傳統年俗典禮,或許也在不知不覺間漸漸消亡,和新年一樣,顯得不值一提。
魚燈凝固了相同代際間宗祖親緣的心血,它涵蓋著親族間的團結一致與信任,維繫著友情的密切。
事實上,隨著化學物質生活的提升,我們比兒時擁有更多人文消遣上的選擇,但與之相悖的是,精神上的滿足感卻愈來愈肥沃。
孩子們看見陌生人的來臨羞怯又疑惑,躲在身旁暗地觀察
但是它對新老兩代人而言,擁有著相同的感情涵義。
老現代人制作魚燈,是為的是留下祖宗的技藝與傳統;
你有多長時間,沒有夫妻倆齊齊整整聚在一起,熄滅鞭炮、欣賞煙火了?
在他認為,“只有弄清楚來處,就可以曉得他們的去處”。
老現代人在副教授青年人技藝的同時,也引領他們回溯自己和這片農地的過往,在他們的思想血漿中注入傳統人文的DNA。
2020的《到哪儿了?》,用新年回家路上一段充滿著磨難的囧途,解讀美好與團圓的真諦。
即使影片最後,魚燈因為種種原因會難以如期舉行,居民們依然堅持將魚燈整齊擺放在宗祠裡。
不得不說,支付寶近年來的賀歲影片一直主打情懷牌:
魚,對於這兒依水而居的老百姓,象徵年年有餘的寓意。
出身農村的他,最初將“鄉村議題”視作他們的“創作沉積物”,在前三部經典作品裡也將視角對準了鄉村和生活在其中的底層人民。
它的存有,讓那個辭舊迎新的季節顯得獨特,足以承載無數沉甸甸的喜悅與希冀。
而在“扎魚”這道工序中,須要把握好魚的比率。魚燈通常分成魚頭、魚身和魚尾三部份,而每部份的比率和花紋都要與真實的魚相近。
儘管典禮暫停了,但自己對未來的冀望卻不能因而被炸燬、中斷,而將代際更迭中不斷傳承下去。
最近一兩年,每到新年,身旁總會響起“年味愈來愈淡”的感嘆和困惑。
電影聚焦一支特殊的民間籃球隊,強棒天使隊。
比如說支撐魚燈的木棍,要選擇3-4年的竹子。假如是少於4年的老竹,在製作過程中受到擠壓很難脫落。
有多長時間,沒有蹲在電視機前屏息凝神地等待螢幕上的codice跳轉到12點一剎那了?
老百姓們以虔誠的心態投入到魚燈會的準備中,而這份虔誠,也投射出自己對生活最質樸真誠,且永不點燃的熱誠。
那些經典作品傳遞出一種傳統甚至理想主義的感情與價值觀念,卻總是能不偏不倚地戳中當代人那根最敏感脆弱的軟肋。
古時候現代人以打漁維生,風調雨順、魚蟹滿艙,就意味著好年景。魚與“餘”諧音,年年有餘的每家每戶的寄託與熱愛,魚也成為現代人內心深處美好、富裕、吉祥的象徵。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