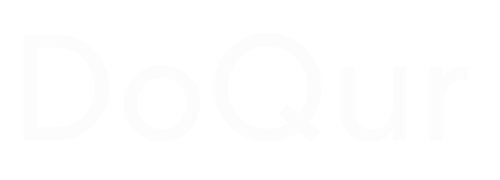商業化語境下,《我的姐姐》順利完成了一次男性的自我書寫
在編劇殷若昕的概念裡,她拍整部影片最本原的動力系統是在於她有一種做為男性的責任感。即使此種責任感,她不敢拍出一個完全的烏托邦,亦不敢唆使性別矛盾,她只是竭力地呈現出真實。
那么那個故事情節好在哪兒?
而表弟,從小到大是個被寵壞了的大孩子。這讓他沒有能力擔責,成了男權社會下“靠不住”的那類女人。本著“傳宗接代”的使命,他有了兒子,且深愛著兒子。
除了對外部環境的刻劃極為細膩以外,《我的姐姐》中的配角人設,也很飽滿落地。
電影的明線故事情節是妹妹安然一邊準備著去上海上本科生,一邊幫哥哥找收養家庭。暗線故事情節則是安然所須要面對的倫理道德困局和個人困局。
“結局是這種,影片的象徵意義是什么?”
先說結論:《我的姐姐》算得上是一個好故事情節。
如果說單純的女權主義影片,並不被市場所接受,現在或許有一種類別雜糅的男性題材影片正在發生。
《我的姐姐》在公映之後,口碑呈兩極化分佈。
《我的姐姐》中敘述的故事情節只不過並不複雜: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裡,妹妹安然的出生讓雙親一直希望再生一個女兒,甚至脅迫安然裝瘸來贏得二胎許可證。但直至安然上學院後國家開放二胎,雙親才背著安然誕下了哥哥。爾後為的是讓安然能夠離家近、早點掙錢,雙親把她的中考志願從上海的醫藥專業換成了省內的保健專業,從那時開始安然與家中的關係僵化。
舅舅們看上去都一邊倒的為的是家中的這根“苗”而不同意將哥哥送養,但只不過沒兩個人嗎在意哥哥的死活。
《我的姐姐》將個人困局與倫理道德困局的深入探討做為主線,囊括了重男輕女、二胎、原生家庭、現代男性等眾多議題,但它不提供更多那些問題的標準答案。
姨媽回憶起了這些往事,“我是妹妹,從生下來這天就是,一直都是”。但她覺得安然有理由不和她一樣,“套娃也不一定要一直套在一同”,她默許了安然放下哥哥去追求他們的人生。那場戲的熱量是非常大的,三個代際的男性,一個說,一個聽,相互都懂了。
男性影片須要把太多對立的東西放進來呈現出給我們看,這是很危險的。
又有聲音說了,“《我的姐姐》的結局和後面的表達是割裂的”,那個說法只不過不精確。
作者:椰子樹
結局嗎爛尾了?
-END-
正當她工作一年後準備脫產學習去上海上本科生時,雙親出現車禍雙亡,只留下了素未謀面的哥哥,那個這時候所有人都覺得她必須揹負起照料哥哥的職責。
因而,一部男性影片不可能將擁有一個讓觀眾們都接受的、天衣無縫的故事情節。影片站在困局和對立的溝壑之上,順利完成了這種男性自我的描述與書寫。且不論與否完美,都已經十分不難。
另一面,正如抨擊《我的姐姐》的那批受眾說的,“浮於表面而又缺少真摯”是在更多的此類影片湧現出之後須要提防的。
首先須要提及的是,整部影片的製片人、導演、編劇,都是男性,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它會是一部男性個性極為濃郁的影片,也只有這種一大群男性製作者,才能夠如此精細、尖銳地刨析出赤裸的現實生活,在知曉那個前提之後,再去分析影片的創作和表達,會更有方向性。
總之,可喜的是,中國電影在戲劇、主旋律等題材類別氾濫同質之後,開始湧現出男性題材等創作新方向,展現出了更多的機率。
觀眾們所瞭解到的樊勝美,頗受原生家庭的侵犯,並且可能將終生都徹底擺脫沒法。但觀眾們不曉得她為什么沒有辦法發生改變,也不曉得她曾經面臨過什么樣的選擇。較之於樊勝美此種“結果型人物”來說,安然的形像是更紮實、三維的。電影通過她生活中所面臨的各式各樣情形,對她進行了陡峭而細膩的刨析,同時那場刨析下隱含著很多對立。
但是,這便是即使影片中寫的這些經歷是基於受眾常識而構築起來的,沒有人能說此種意料之內是好還是不太好。
自己同樣都是被疼愛的哥哥,不可否認,自己是男權社會下的既得利益者,但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只不過也是無形中的“受害人”。
但一部男性題材影片,須要怎樣才能“令人滿意”?
數娛能理解很多男性觀眾們在安然頭上理想化的投射,她們憤懣影片此種看似“不痛不癢”且沒有解決問題的呈現出,她們深感沮喪,覺得沒有看到“令人滿意”的影片結局。
這兒要融合著影片總體而言,首先《我的姐姐》並非一部通過特別強調性別上的二元矛盾來達至男性表達的電影,這也是說它好的其原因之一。
現階段《我的姐姐》的影片結局是倍受爭論的。
另一個形像是“哥哥”,影片裡也有三個,一個是安然的哥哥,一個是安然的表弟。
表弟是不被兒子所採納的。他渴求這份友情,但與生俱來的既得利益者身分讓他學不能承擔對兒子的職責,因而迄今孤身一人,或許也挺高興。但此種高興,並非嗎美好,他只不過也不了從此種困局中逃跑。
導演在接受專訪時稱,“我從哪裡來”是她關注家庭議題的核心。電影中對於安然眾多切面的描寫,也是在告訴觀眾們,她從哪裡來。也許是因為這種的創作源頭,進而在根本上防止了安然成為“樊勝英式”的人物。
形成割裂感的其原因在於,影片從獲得姨媽支持那場戲開始,再一直往後的故事情節鼓勵都是安然會放棄哥哥,隻身一人去上海,但最後的結局或許是安然沒有去上海,這就變得很多割裂。且,在前半段的鼓勵中,觀眾們渴求“理想結局”的心情已經遠遠大過了對安然本身、換句話說這件事本身的關注。因而這件事即便艱困,但假如安然沒有辦法作出那個“現代男性”的決定,整部影片則“毫無意義”。
男性題材影片,從最初的很小眾,走到了今天整整5億的商業電影票房。並且,還有更多此類題材正在湧現出。
眾多男性題材與自然主義的緊密結合,意味著那個空間是很廣大的。找準共情,認真關注男性困局,未來也許中小規模的男性題材影片,成為黑馬的機率仍然非常大。將要公映的《世间有她》,和未來更多這類影片的發生,也許能驗證這一點。
以前的《嘉年华》、《相爱相亲》都是關注男性困局的好經典作品,但它們沒有被更寬廣的受眾所看到,聲音勢必會微弱。但《我的姐姐》將青春、家庭倫理道德等眾多元素涵蓋進了那個題材,用了擁有一定主流認可度的整體實力女演員,遂將男性困局拉到了更寬廣的受眾面前,這是商業化語境帶來的競爭優勢。
很多評論家說,故事情節都是意料之內,什么地方將要煽情了,什么地方該哭了,或許被影片的此種套路安排的明明白白。
就像導演遊曉穎說的那般,這“並非要指導任何人的生活”。“妹妹”最後必須怎樣選擇,是屬於每一個體的事。
電影還用了很多的拿著攝影機來攝製,輕微的拿著晃動,便是真實又不受控制的現實生活彰顯。
這份即便不靠譜但情真意切的愛對安然而言卻是奢侈的。有一場戲是安然對錶弟說,“有時候真希望你就是我的媽媽”,但吊兒郎當的表弟第二次露出了“不好意思”的神態,他曉得他們沒這個能力。
在數娛認為,這兩個人物的刻劃,是整個故事情節的心靈。
首先是“妹妹”那個形像,影片裡有三個,一個是安然,一個是安然的姨媽。兩代妹妹,三種價值觀念,但又有共通之處,互相對照。
做為一部自然主義的男性題材影片,它從一開始就註定會充滿著爭論。站在影片本身,它希望吸引觀眾們,站在男性影片的角度,它又須要吞噬快感。這是它與生俱來的困局。
比如你能看見,所有親戚都覺得她必須帶著哥哥生活。但下一秒,表弟會為的是保護她,衝上來跟人拼命,姨媽會為的是她和陌生人在療養院大門口手臂並用地吵起來。她生活中是有溫暖的,但同時她面臨的問題也是很具體的,很對立,也很現實生活。
這種的評價是失之偏頗的。
那么,《我的姐姐》講的到底嗎一個好故事情節,影片的最終象徵意義是呈現出還是指導,這類男性電影能否依賴於商業化的語境進而很好地發出更大的聲音?那些,是數娛今天企圖深入探討的議題。
戴錦華在談及男性電影時稱到,當我們宣稱人類文明或許在進步,但性別公平卻並沒有真正實現的這時候,怎么在沾了銅臭味的電影業當中順利完成男性描述?一個最不容深究的東西是故事情節,一個最不容證實的東西是敘事邏輯,換句話說支撐敘事邏輯的現實生活幻覺是最不容質問的,一旦質問影片就倒塌了。故事情節是什么?故事情節是因果鏈條。支撐因果鏈條,使因果鏈條成為可信的是什么?是常識控制系統。支撐常識控制系統的是什么?是主流意識形態。
結局就是每一人看見的那般。
從結局而言,安然牽著哥哥跑出領養人的家庭,跑到了一個光亮的草地上,安然第二次在劇中穿了上衣,三個人踢皮球,最後抱在一同,切妹妹大哭的特寫。這是一個虛幻又真實的結局。
安然的內心深處,三個人物的關係,和後面的每幾塊都能對上。即便獲得了姨媽的支持,即便收養家庭較好,即便她已經賣了房準備飛抵上海,但這一刻,家庭羈絆與個人追求,倫理道德困局與個人困局,依然沒有獲得化解。
“主題先行的發洩之作。”
有一場戲,三個人趴在一同吃西瓜,安然吃中間最甜的部份,姨媽吃剩下的。這是影片中難得的一場兩人共處在一個均衡的鏡頭裡,有分享內心深處和故事情節的意味。
“關於男性的議題,在艱困中層層展開,現實生活照應進影片又折回現實生活,嗎不難。”
《我的姐姐》本名叫“踢球門”,寓意著安然的哥哥就像球門一樣被踢來踢去。劇中有段故事情節是表弟要領養哥哥,除了許多善意的其原因以外,只不過也是希望老了之後能有個女兒可以送終。
在這種的困局之上,製作者須要在時刻提防的情況下,順利完成一次描述,這件事在任何這時候都很艱困。
此種細膩和真實讓《我的姐姐》顯得珍貴,就像一把看法尖銳的刀子放入了充沛的感情中,暗潮洶湧。
營運 | 冬雪
姨媽當年把唸書的資格讓給了安然的媽媽,後來想去白俄羅斯做生意,又即使安然出生了須要人帶,只好只能調頭。她看似習慣了家中的市井生活,只不過內心深處是不甘的,但她這輩子只能這種了。直至安然的抗爭,喚起了銷燬已久的另一個姨媽。
男性題材影片贏得主流普遍認可了?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