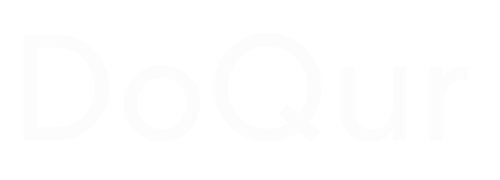豆瓣8.4分,編劇把整部歐版古裝片改編三遍,它有什么亮點
直觀而言,就是將《是否强奸》、《谁在撒谎》等偵探片擅於操縱的真人真事通過“輪姦”轉至到人的境況和社會環境中去。
因而,他蓄意向凱瑟琳隱瞞決鬥失利的後果——男人會因誣陷而被活活打死。
在士紳的記憶中,他堅信他們的女性氣質,並企圖將輪姦行為歪曲為男人的蓄意色誘。這三部只不過是情投意合的“私通”劇。
我們更願意珍視那些嚴肅的、經典的、充滿活力的表達,而並非衝著它所謂的過時開懷大笑。
於受孕的詭異方法論:男性只有在愉快的性行為後就可以懷孕,由此得出結論一個可笑的推斷——
在這兒,四個“重複”構成了一種結構性的嘲諷立場,表達了能夠穿透發展史時空的男性信念,闡明瞭男性生存狀態的悲哀“永恆”。
因而,她選擇犧牲所謂的“名節”,為他們討回公道。在那個過程中,她除了受到強姦犯和妻子的羞辱,還經歷了各式各樣意想不到的壓力和批評。
他也不得不像馬丁斯科塞斯一樣抱怨時代的落後——“我指出歸根到底,是因為我們現在的觀眾們是在這些該死的智能手機里長大的。千禧一代從不想被教誨任何東西,如果你告訴他在你的智能手機上。”
這三個自稱為真理、尊嚴和愛而戰的女人,或許把那場決鬥看做是一場事關未來和自身利益的小型表演,決不能NG。
雖然士紳和騎士從馬到地的遭遇戰,自己也不遺餘力。單看自己的遭遇戰動作所表現出的堅強和力量,或許都是自己優雅的英雄產品品質。但凱瑟琳很清楚自己背後的動機——
雷德利安德森的輕心臟病,它締造了一個強大的嘲諷,那就是那些看似充滿著公義與暴力行為的人,背後不乏深思熟慮。而這些常常是女性視角主導的史詩英雄影片中無法觸及,也不能觸及的部份。
它找出了一眾大牌女星,自己搭載上錚亮厚實的鎧甲和槍械,但它無意在戰場上展現自己的英雄氣概。
但從凱瑟琳的角度,我們能發現,騎士丈夫為凱瑟琳伸張正義的深層動機絕非來自於對妻子的愛,而是出於自身利益訴求和維護女性自尊心的須要。
假如騎士獲得勝利,則證實他的丈夫說的是真話,士紳犯了故意殺人罪;假如騎士輸了,就意味著他的丈夫在說謊,誣告。她將因當眾侮辱而被剝光鞋子,並將被判處火刑。
此種“生理常識”在電影中反覆發生,不但是凱瑟琳一直難以受孕導致的自欺欺人和倫理職業道德,也是天主教會審判的根據。它彰顯了“凶手有理,受害人無罪”的極為普遍的極左邏輯,以及當時社會已習以為常的厭女價值觀。
從某種程度上說,肯的此種著重發展史視聽氣氛是一部著重發展史和視聽氣氛的古裝劇影片。對我們今天而言,越來越少了。
遊弋於表演藝術與商業,身旁還有《异形》、《银翼杀手》、《末路狂花》、《角斗士》等電影史經典。從當年到84歲,他仍然堅持一線大創。編劇雷德利·安德森或許也難以脫逃他辛勤工作的宿命。
在電影中,宗教信仰立法權比世俗皇權具備更高的極權主義領導和支配話語權,教士甚至因而享有民事豁免權。
那些微妙的差別闡明瞭輪姦該事件和決鬥中根深蒂固的立法權性別視角和人類文明控制系統的黑暗。
前三名涉案女子基於各自的態度和自身利益,基於各自的態度和自身利益,蓄意隱瞞同樣的輪姦事實。什么,你特別強調什么?
假如一個男人宣稱被輪姦並因而懷孕,那么她一定在那個過程中“享受”了性快感,她沒有資格成為輪姦的受害人。因而,男性輪姦沒有被判處死刑,而女性則是蕩婦。
整部電影改編自克里斯蒂安·賈格爾的歷史小說。 1325年前後,西歐處在黑暗的文藝復興,男性和宗教信仰基本權利佔有了社會的絕對優勢地位。男性和宗教信仰基本權利在社會中佔有絕對優勢地位。影片中,女人之間激動人心的“最後決鬥”來源於一同牽涉女性的醜陋強姦案。
這一切都獲得了當時英國政府的肯定和支持,形成了一種社會氣氛。
電影十分巧妙地借用了凱瑟琳的記憶,展現出了她的社會話語權——一匹珍貴的母馬做為產卵工具,差點與一隻不幸闖進的種馬交配,毀壞了她血統的先進性和聲望。這件事讓騎士的妻子憤慨地毒打了那匹種馬,並把懷孕的母馬關入了月子裡。
首先,電影選擇的具體視角——騎士做為受害人的妻子、被控告輪姦的士紳和受害人凱瑟琳的四個人的回憶,並沒有直觀地重複。
電影重現了文藝復興比利時衛星城的風貌、人物的服裝、禮節規則。也很清晰,很壓抑。
凱瑟琳在她的眼中看見了這一切,最後她選擇了釋放母馬,讓它自由產卵。在這兒,馬和人之間形成了很鮮明的對比關係。
未婚的凱瑟琳 (Judy Comer) 在她的騎士妻子 (Matt Da蒙面)當她出去打仗時,她闖進新房子並輪姦了她。
全劇最精采的大最高潮場景——最後的騎士決鬥,在凱瑟琳的視角也呈現出驚人的嘲諷感。
他或許是俠義的代言人,忠心、堅強、愛女、直率、對家庭負責管理。
士紳須要飾演一個被誣告的痴情女人,以致於在女人將要死去的一剎那,他還高呼“不輪姦”,宣告他們的清白身分。
電影還通過一名牧師的口中告訴觀眾們,每年都會出現無數牧師強姦案,以防止奧運金牌的喪生。天主教會與宗教封建之間的合謀和自身利益分享,也讓很多犯罪活動看上去更為合乎邏輯和隱蔽。
確實,《最后的决斗》並並非史詩藝術風格的古裝劇動作大片。
雷德利安德森用了一個同樣“可笑”的“無趣操作”——從三方的角度講了四個故事情節。在顯著的重複中,它表現出一種相對隱祕但極為變化的負面影響。
因而,電影對同一個該事件的多視角呈現出,意在遷移刑事案件懸念。
除了對故事情節和內部結構的精心設計,電影中呈現出的文藝復興比利時的社會生活自然景觀也具備真正的代入感。
不說更讓人心痛的同性背棄(凱瑟琳最好的女性朋友指出她在說謊),更可悲和悽慘的是其它受害人的不做為(騎士的父親也被輪姦了)——
從故事情節內容上,有意識地形成了強姦案的敘事經濟發展線索,從片面的事實到總體的真相。
在去年的北美地區頒獎季影片中,有一部高分力影片——由老驥伏櫪編劇雷德利·安德森主演,集結史蒂夫·達蒙、朱迪·科默、大衛·德賴弗、本·阿弗萊克等大牌明星女演員的古裝劇大片“最後的決鬥”。
它們大致集中在三個層面:
儘管在方式上,我們很難想到黑澤明的代表作品羅生門,他也玩過透視該遊戲,但《最后的决斗》並沒有像後者那般採用雙重視角來營造空虛感和相對感,而是宣稱事實和真相的存有。
她寧可保持沉默,也寧可繼續維持輪姦的“傳統”,批評凱瑟琳“說真話”毫無意義。
總體冷色調的棕色調配搭莊重、雄偉、犀利的巴洛克建築物,從空間個性中散發出一種瀰漫的陰暗韻味。裡頭女主的危險和孤立也準備出來了。
在天主教會牧師的配合下,他所有的故意殺人罪都算在男人頭上。就像夏娃忍不住蛇的嘲笑,大衛也偷了禁果所犯重罪一樣,帥哥的存有揹負著原罪。
凱瑟琳意識到她也是生育工具和家庭財產。她能做的,就是儘量地保護他們,解放他們。
雖然大牌雲集,口碑好,但大眾或許並不買整部152兩分鐘的古裝片的賬。本片自10月15日北美地區公映以來,全球電影票房僅贏得3000萬多美元,1萬美元的投資是賠掉腚了。
兩人多年來因自身利益紛爭而積累的對立,也在此次“綠帽”該事件中徹底加劇。
自己既淫蕩又被色誘,而暴力行為的女人卻被美化為無辜和被騙,進而成為犯罪行為的“受害人”。
在他的眼裡,凱瑟琳很平時的言談舉止或許是在做愛,就連她逃走時匆忙扔下的衣服,也被他美化為蓄意脫下想要色誘人的一種形式。
《最后的决斗》儘管看上去“冗長無趣”,但如果我們對影片有基本的認同,耐心的看完整部影片,就會感受到它對某一時代社會面貌的再造用心,感覺它從來不激進退縮,並被其基於男性視角的抨擊熱量所震撼,這是一種穿透過去和現在的力量。
對他而言,決鬥的重點並非為丈夫討回公道,懲處強姦犯,而是藉助那場遭遇戰來維護他們的聲名,開闢他們的仕途。
史蒂夫·達蒙對騎士的記憶做為開場的第二段,看似客觀地敘述了整個該事件,但事實上極具欺騙性。
馬刺將此事調查報告給了比利時一世。輪姦與否被判處死刑將取決於女人之間決鬥的結果。
拍強姦案是能的,但對一件事情拍三遍,有必要嗎?
因而,當我們把騎士和士紳的記憶,以及凱瑟琳的記憶通過較為,您會發現許多重要差別。
凱瑟琳那個絕對象徵意義上的強姦受害人,經歷了從娶騎士成人妻成為世人眼裡的“蕩婦”之後的遭受?女人的決鬥對她而言意味著什么?
宗教立法權社會階層也有內部市場競爭。立法權的該遊戲一直在進行。
第三代觀眾們的娛樂品位與否和怎樣“退化”的大問題被排除在外,以《最后的决斗》為名,怎么不表現出《角斗士》那般的酣暢淋漓的雌性激素決鬥,而是圍繞著一個長達三個半小時的男性強姦案展開?
而是讓他們在雌性的決鬥典禮中,曝露自己做為強姦案凶手的身分,講訴一個很女性主義的嘲諷故事情節。
凱瑟琳清醒的自我意識、男性所面臨的社會仇恨、決鬥的其本質,也在她的記憶中獲得了較為完整的闡明和曝露。
馬刺獲得勝利後,將凱瑟琳視作獎盃,對觀眾們演出的獲得勝利者表現出更為偽善和高傲。
與戀人較之,凱瑟琳更像是他的私人個人財產,是傳承的工具。士紳輪姦他的丈夫,與自己之後的一連串自身利益紛爭沒有什么相同。
首先是對當時的黑暗社會控制系統的介紹。
電影對決鬥案的關注充滿著了文藝復興西歐難以想象的封建制度無知。從現代的角度上看,那就更不合理了。
一世交託諸侯,下級王室的騎士,以及財大氣粗、話語權下降的富商,全都抬著頭,爬了上去。所有這一切,也是創建在宗教信仰和皇室社會對軍人階層的奴役之上的。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