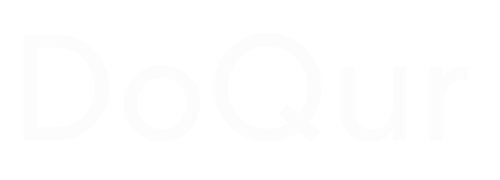那兩年奧斯卡金像獎,面對張藝謀6億鉅製,評委將最佳頒給一部30萬小片
電影感情的複雜性從這兒就始見端倪。
只好肇始於1925年的土耳其影片始終發展緩慢,題材上始終放不開手臂,我們常說的那句“帶著鐐銬唱歌”也是對土耳其影片狀態的直白敘述。
等到納德回來時,瑞茨問他:“你為什么不早告訴我你母親會失禁?”
故事情節經濟發展就是這般美妙,沒有好人與壞人之間上演的劇烈紛爭,有的只是正直的現代人在各式各樣其原因的束縛下,違心地相互批評。
而在敘述這部分時,電影又一次借用小孩視角來“追本溯源”。
就像《偷自行车的人》裡這個見證了母親偷車又被抓,依然牽起母親的手的小女孩一樣,特梅在11六歲時知道了,他們的母親會說謊會推卸責任,並並非一個完美的人。
丈夫納德自然知道妻子的疑慮,但他卻不願意移民,即使他的母親罹患老年痴呆,須要他照料。
西敏鬆垮的鮮豔長袍上面露出了火紅的指甲、頭部和腰部。
比如說路易斯·帕蘭德《我在伊朗长大》中這個在土耳其社會動盪不安中成長的女孩瑪嘉。
似乎調解員這個問題不但是問西敏的,也是問觀眾們的,特別那個國家的觀眾們。
此外,假如你注意觀察,整部電影中的地板也尤其多。
雖然《一次别离》沒有故意去抨擊,但是從影片攝影機、人物造型、臺詞等各式各樣影片詞彙中,我們都能深切感受到土耳其“分裂”社會下兩極分化、社會不公正等“土耳其現實生活”。
片末,三個家庭庭外和解,西敏和納德還是再婚了。
當特梅告訴檢察官,母親確實不曉得瑞茨懷孕時,她或許“長大”了。也便是在這一刻,特梅喪失了他們的兒時。
西敏才是這個一直在默默地照料納德母親,一直冒著犯禁的信用風險幫他清洗皮膚更換鞋子的人。這也解釋了,為什么已經幾乎失去說話能力的納德母親,會一直嘟噥著西敏的名字。
那么問題來了?
但她依舊愛他。
但從電影結尾這幕長鏡頭中,我們還是能夠判斷出一點,不論是西敏還是納德,都並非壞人。
聽見那個問題之後,納德很吃驚,急忙則表示他們並不知道,他一直以為他們的母親是能他們上洗手間的。
瑞茨以哈里發·穆罕默德的名義誓言他們沒有偷錢,納德卻抓住她的黑頭巾,把她面世了門前。
為的是能讓母親在下班時有人照顧,納德請了一個保姆瑞茨。
並且,瑞茨還大著肚子,她是瞞著他們的妻子出來工作的。家中欠了一大筆錢,妻子又失業,她只能這么做。
瑞茨的兒子和特梅三個小孩,一個親眼目睹了家裡的貧窮,和母親的假摔;另一個忍受了雙親鬧再婚以及幫助父親說謊的壓力。
問題在瑞茨下班的隔天就發生了——納德的母親會尿褲子。
這是一種先驗的預設,再加上後天不斷的重複,直至此種悖謬的看法顯得再自然正常但,至此才真正成為社會的一部分。
比如說馬坎比·馬基迪《小鞋子》中那對來回交換一雙衣服穿的姐弟。
在調解未果後,兩人選擇了同居,西敏搬到雙親家住,特梅選擇了和母親曾祖父同住。
西敏沒有說話,維持了沉默。
這時候調解員就問了:“什么樣的環境?”
而瑞茨也同樣面臨著納德的起訴,牢獄之災近在眼前。
劇中,當特梅在高等法院的走廊跟著外公自學土耳其發展史時誦讀到:“在薩非王朝時期,現代人被分割為三個社會階層:下層特權社會階層和普通社會階層。”她的外公糾正必須是“普通群眾”。
而此種分裂下的差異性也延展到了三個社會階層對於宗教信仰的相同立場。
三個人站在門前,卻隔著兩層地板,彼此間都惴惴不安地等待著兒子提問這個凶殘的問題:“跟爸爸還是跟媽媽?”
《一次别离》丨2011
生活並沒有在這件小事後恢復平淡,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兒子已經作出決定,但編劇仍未告訴我們答案,電影也在一個未知悉的選擇中落下帷幕。
但在三家大人鬧得不可開交時,納德依然俯下身來拉住瑞茨的兒子告訴她:“別讓父輩的鬥爭危害你。”
而攝影機的另一側,便是瑞茨的小兒子,她在下意識地重複著那些晦澀難懂的語句,從眼神上判斷,她並不理解語句的涵義。
事情至此再明白但,紛爭之中的二人誰都曉得真相,可又都不肯講出真相。
為什麼他母親剛好等到那個這時候才發生此種情形?
所以,這種的電影劇本設計一方面是要避免審核,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受過較好基礎教育的中產階層家庭想要返回土耳其,是一件不須要任何理由和解釋的事情。(比如說《我在伊朗长大》中的瑪嘉,14六歲時就被雙親送至了匈牙利。)
瑞茨卻總是用白色長袍把他們的指甲、肩頸裹得異常嚴實。
《一次别离》是一部十分傑出的影片,它並不只是在講一個家庭,三個家庭的故事情節,而是在講訴整個土耳其社會的故事情節。
一部又一部幼兒經典,讓人對土耳其影片刮目相看,但土耳其人對“幼兒題材”的偏好,只不過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納德大發雷霆,責罵她把他們的母親一個人回到家中,還說她偷錢,並且則表示讓瑞茨之後都不用以了。
從宏觀經濟角度而言,這是法哈蒂的勝利,同時也是土耳其影片的勝利。
而藉由個體人的自我分裂,土耳其社會階層層面的分裂也一望而知。
《一次别离》中,中產階級與社會底層之間的分裂早已是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此種現實生活的無力感會讓人極其壓抑。
從這兒開始,兩家人鬧上了法院。
再如阿巴斯《何处是我朋友的家》中,這個翻山越嶺,從夜間找出黑夜,只為把裝錯的作業本送還給同桌的小女孩拉扎。
納德說謊了,他曉得瑞茨有身孕,推她是因為他當時氣昏了頭。假如他嗎入獄了,母親怎么辦,兒子怎么辦,他只能咬死不承認。
同時它向我們證明了:戴著鐐銬,同樣能跳一支好舞。
果然,隔天,西敏告訴納德,瑞茨流產了,即使那一推。
平板地板、壓花地板、鋼化地板、磨砂地板、防彈地板......一層層的地板不但分隔了社會階層與社會階層,同樣分隔了情侶和家庭成員。
攝影機跟隨著西敏穿梭,看似不經意地掃過家裡的佈局和陳設,小提琴、計算機、臥室的油畫經典作品、乾淨整潔的廚具等,充份表明了納德與西敏中產階級的社會身分。
之後,當納德為母親清洗皮膚時,他開始坐在母親的背上失聲痛哭。
至此,故事情節陡轉。
從那一刻起,新生兒已經沒了動靜。
瑞茨的兒子眼裡所散發出的偏見的表情宣告了三個階層間的非常大鴻溝。
瑞茨是一個虔信教規的上層階層婦女,迫於生活,每次都會帶著她的小兒子索瑪耶來下班。
瑞茨把《古兰经》看得比流產的小孩還關鍵,納德卻能對著《古兰经》說謊。
瑞茨也說謊了,她的流產並非納德引致的,而是前一晚在納德母親偷跑出家門時,為的是不讓他被路邊的車撞到,瑞茨他們被車撞了。
納德堅持說他們不曉得瑞茨懷孕,只是為的是讓她返回他們的家才推了她一下。同時他還說,即使當時瑞茨私自返回把老人家獨自一人綁在床邊,差一點引致他的喪生,而且他們才情緒興奮推了一下。
但瑞茨的家裡,則是破爛的椅子、破損的牆壁、破舊的茶具和狹窄的浴室。
對瑞茨而言,錢關鍵,但尊嚴更為關鍵。薪水必須要。
有一天,納德提早上班返回了家,發現母親倒在天花板上,神志不清,一頭手還被捆綁在床邊,差一點殞命。
假如納德明知瑞茨懷孕還推她,那么等待他的將是一到五年的拘留所職業生涯。
對於擅離職守這件事,瑞茨並沒有做出駁斥。而當她聽見納德說她偷錢的一剎那,情緒開始興奮起來,並堅持索取他們兩天的薪水。即使這是她的勞動所得,假如千萬別薪水,就表明她心虛了。
而在三個小孩的成長環境中,此種社會底層家庭與中產階級的分裂及差別,也以簡單、赤裸的形式呈現出來。
在土耳其信奉的教規教法中,一個男人只容許為他們的妻子和女兒清洗皮膚。假如瑞茨幫納德母親洗了,那么她很有可能會因而犯禁。
兩方各執一詞,也許我們會猜誰說的是嗎,但是真相卻是三個人都說謊了。
影片始自一個小法院的場景,短短的幾秒鐘,就極為值得玩味。
並非。
上面提及的兩部影片是這種,下面要說的整部影片也是這種,借小孩視角直面土耳其一連串敏感問題,如社會階層對立,如男性問題,而其故事情節下獨特的教規大背景和現實生活表達都可說是土耳其國內不折不扣的大尺度——
你看,社會階層與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從小孩時就已經在潛移默化地出現著了。
前一秒還在屋子裡一同嬉戲的三個人,這時卻即使父輩階層之間不容調和的矛盾而坐在了彼此間的對立面。
父輩的鬥爭,最終還是無可避免地危害了小孩。
特梅的雙親甚至是外公都可以指導她的自學,即使自己都是受過較好基礎教育的知識分子。但瑞茨的小兒子,只能背著小書包跟著爸爸去打零工,只能吞嚥著這些生澀的關於“階層矛盾”的語句。
為的是更為溫和地表達看法而又不違反教規後的倫理禁忌,“幼兒題材”以及幼兒視角的影片成了很多編劇創作的最佳載體。
藉由一名沒有列入攝影機的調解員的視角,我們親眼目睹了兩對中產階層妻子申辯自己提出申請再婚的理由。
提起土耳其影片,我們腦海中浮現的總是一個個幼兒的形像。
西敏為的是讓小孩接受很好的基礎教育而移民,納德為的是能夠陪伴在母親身旁而並非假手於人而婉拒移民,三個人的理由都很正當。
至於為什麼大哭,也許只有納德他們知道,但這或許也預示著,將要會有大事出現。
也只有西敏離開了家,納德才會曉得真相,曉得丈夫的不難。
答案也是不言自明,但編劇這兒還是採用了留白的表現手法,省略了關於土耳其政局動盪不安和核危機等敏感話題的正面表述。
納德的原意是好的,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但危害也確確實實出現了。
在電影最高潮爆發的時刻,三個男孩的視線相交了。
土耳其是一個為專制為上的國家,影片受到了教律的雙重負面影響和制約。
原來懷孕的瑞茨扔下老人家去辦他們的事情了。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