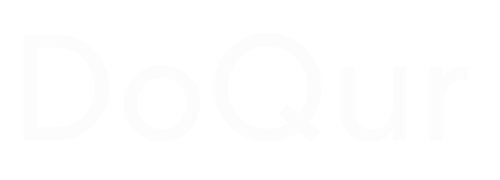從立項到公映 主旋律影片怎樣拼出“中國速率”
戲裡,中國人民志願軍要趕在下午四點之後過河就可以趕上金城會戰;戲外,全組5000多人也要在非常有限的時間內拍完電影。是所有人長達四個月的咬牙堅持,很難複製。《金刚川》背後是5000人奮勇渡過影史上的“金剛川”。聯合編劇田羽生迄今指出,《金刚川》能拍成電影也是一個奇蹟,我們都在探討“中國速率”的概念,但並非說每一電影都能這么像《金刚川》這種,天時地利人和,應運而生:“首先是管虎編劇有這種一個創意設計,能夠調度一切資源多視角攝製,並在短期內能夠讓兩個團隊同時動工,我們的團結一致讓這件事情才有可能順利完成。《金刚川》是中國電影工業體系成熟條件下的一個產物,這是一次具備里程碑式象徵意義的實戰經驗,對於中國電影而言,也是一部很有紀念象徵意義的影片。”
去年8月殺青,10月23日就公映。做為一部大製作的戰爭片,《金刚川》製作工作效率更讓人難以置信。回顧過去多年,兩部關鍵的中國主旋律電影都締造了“中國速率”的攝製奇蹟,而那些奇蹟便是創建在中國電影日益城市化的程序和技術基礎之上。能說是日漸成熟的中國電影工業體系幫助了主旋律電影取得了商業上的巨大成功,而主旋律電影也在另一個層面重構著中國電影市場。便是有了那些強大基礎和中國電影人不懈的拼搏努力,我們的電影市場才得以在多年的時間裡,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不斷通過“中國速率”締造出《建国大业》《决胜时刻》《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和《金刚川》等電影票房口碑都取得成功的主旋律影片。
《我和我的祖国》創下了獻禮片的新高度,不論內容表達、影片票房戰績或者觀眾們口碑均獲得了主旋律影片新的成功,並形成全民的觀影風潮。在一個多月時間內孵化出來的經典作品,多少人在做之後都指出是空前的嘗試、很難順利完成的任務,但張一白說做這種的片子本身只不過沒有那么多難以想象的困難。“一旦收到任務,在製作電影劇本的這時候同時進行相應的工作的積極開展。中國影片工業經濟發展到今天,整個產業發展體系梳理得較為明晰。在成熟的影片工業體系下創建的工程項目,加之每位編劇本身具備的多樣實戰經驗,我們創建起相應的成熟團隊,同時每一參予者都有想參予創作的熱誠,那些要素一有,只不過在製片人層面上來說真的算不上難。”張一白則表示,假如非要說最難處理的通常都是在創作上,對白怎樣雕琢,歌劇怎樣精采,這才是永遠須要精益求精的方面。
南方週末本報記者 周慧曉婉 滕朝
《我和我的祖国》、《一点就到家》那些經典作品都是中國速率的一個彰顯,而中國速率那個概念在張冀認為,越拍越快的時代要保證質量可靠,現階段的環境下也是須要拍這種的影片,也須要用此種速率拍影片。對於製作者而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環節順利完成好自己的分內工作。“誠然,壓力是非常大的,壓力下要找出相應的應對形式,比如《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相遇》歌劇,很大的先決條件是在創作上、表達上與編劇達成共識,這種能較為快、較為穩地去執行。”張冀說,中國速率能成功的基礎還在於要有創作基礎,在人物上儘可能真摯,他回憶在創作《相遇》時,僅是收集資料就讓他非常敬佩,或許被帶回七十二十世紀兩對普通戀人面前:“這類主旋律的影片,並非說就是個任務,只想著交差,而是要步入到某一發展史二十世紀的現場,步入到普通人的頭上,他們平凡也有不平凡的經歷。成功的主旋律之所以成功,最重要是彰顯到人性上的。”
“空前”,則是藝術指導嚴書恆回顧《金刚川》創作之路時提及次數最少的詞彙,迄今回想起來,那種現場攝製的緊張感都歷歷在目。在收到工程項目的時,很緊急就已經刻在了嚴書恆等片場人員的心底,那時,各個主創人員在各個相同的地點開視頻會議,到復景後很果斷大力推進怎樣製作的重大決策,迅速大力推進的快速感,所有出現的一切都是空前的。“要說中國速率,我覺得這就是中國人的速率。我們的少數民族從來就是一個高效率,且忍耐力與爆發力兼有的少數民族。這種一部與時間賽跑的影片,從一開始就轉變了傳統的製作思路,將複雜感情精簡為以犧牲為主題的創作思路,統一全組方向,並初始化多方資源、團隊、技術等,嚴密統籌配合攝製與製作的時間,高效率順利完成攝製任務。”
記得在《金刚川》開機之後,片場的主創人員趕赴營口烈士陵園紀念緬懷先烈,這天讓攝影指導羅攀體會很深刻,“當時我的感想就是,無論是多少人來做這個事情,也無論你怎么去定義此次創作。在抗美援朝的那個二十世紀,至少那些戰士灑過鮮血,付出了他們的心靈。較之那些,我們大家為這個影片付出的汗水與疲倦,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情。那既然這種你沒有理由不把它拍好,也應該、要把它拍下來。”開拍後調完色,第二次看成片的這時候,羅攀覺得《金刚川》遠遠超過了市場預期,可能將在內戰思考的描繪方面很多惋惜,但這么短的一個時間內,這么多傑出的創作人員在一同締造了一個不可能將順利完成的任務,成色還不錯,也對得起觀眾們就很滿足了。
吳京、管虎和張譯在探討《金刚川》電影劇本
11月06日17:18
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就順利完成攝製,影片劇本雕琢時間不少於四個月的《一点就到家》,也給了編劇張冀太多意想不到。專訪中,他反覆提及“時間非常之緊,非常之趕”,怎樣在非常大的壓力與緊張感下確保工作效率,對此他深有感悟:“《一点就到家》是我截至現階段編劇的工程項目中最快的一個。第二次看見成片的這時候就遠遠超過了市場預期,很多這時候能在這么緊張的環境壓力下把一個片子製成,你真能感受到團結一致有多關鍵。那些年,中國影片的經濟發展是非常豐厚的,工業體系初具規模,經歷了這么十多年,國產片對人員的培育、對市場的研發上都一點點打造出他們的話語權,人也在創作實踐中鍛鍊身體出來,這是很關鍵的其原因,即使最終須要靠人、靠實戰經驗。”說到這兒,他的表情堅毅,話語裡還充斥著當初創作時的“緊張感”:“影片人、影片業、觀眾們都跟著國產片的製作者一同成長,比如澳門導演和內地女演員的融合度也非常高,我們都相互重大貢獻著實戰經驗和力量,影片還是要靠影片人,沒什么不可能將的,製作者最開心的還是你的影片被觀眾們討厭。“
從去年的《我和我的祖国》到今年的《我和我的家乡》,張一白感嘆甚深。對現如今業界都在深入探討的“中國速率”有何觀點,他誠懇地談了談他們的想法,這五個字,還是得取決於是不是成熟影片產業發展體系的支持,是不是成熟團隊與成熟編劇的努力和拼命,有了那些才有可能將在短時期內順利完成不可能將順利完成的任務。“主創人員的熱誠、團隊的協同、產業發展的支持,這四個是能無法實現中國速率的必要不利因素。”
《金刚川》中攝製“架橋”
要靠人、靠實戰經驗,沒什么不可能將
每一步都要尤其清晰、高效率
南方週末通過對導演黃建新、張一白、劉偉強、徐宏宇,編劇張冀等以下主旋律電影主創人員的專訪和素材重新整理,從那些電影的立項、劇本創作、勘景道具準備、女演員建組、攝製、後製等重要環節的展現乃至公映後的感悟,聆聽自己創作“提速”背後的艱苦與先進經驗。
《金刚川》的成功也是中國影片的巨大成功,發展史上幾乎沒有這么快的攝製實戰經驗。對此,趙寧宇感慨萬千,他說現在華語影片是愈來愈好、愈來愈成熟,這種才讓主創人員團隊有基礎來實現那個誰都指出是不容能將的事情。《金刚川》的每一步都要尤其清晰、高效率地進行,兵來將擋水來土掩,這一個空前的“快速率”製作真的不能有緊張和壓力嗎?趙寧宇對這種的問題總是搖搖手說“不能”:“假如有壓力和緊張就不能幹了,國家把那個任務交予我們,並非隨便就能夠應允的,假如應允,一定要有把握。”回憶起攝製的幾十天,整個主創人員團隊幾乎是沒有睡覺,連飯都吃不上,每晚天亮就接著投入工作。在趙寧宇認為,這是文藝工作者必須盡到的職責,順利完成那個不容複製的任務,並非出席製作者的勝利,而是中國影片工業成熟的助推:“以前許多電子設備、技術我們都沒有,就像現在有《流浪地球》的團隊,比如說現場怎樣爆破、照明彈怎樣加量,太陽光、美感怎么調試,各方面都很成熟,大家分工各司其職,只有一切都‘穩’,才會有現在的成片。”
《我和我的祖国》之《相遇》海報
快速率會不會有壓力,也是我們反覆質問黃建新的問題,極短的攝製週期,從迅速共同組成工程項目創作團隊,再到正式殺青趕赴11個相同地方攝製,和遠赴白俄羅斯買來五十年前開國大典的彩色膠捲並進行4K高畫質復原融入影片,《决胜时刻》攝製的每一步都在黃建新“每晚只睡兩半小時”的堅持下漸漸成型,談到此他輕描淡寫地提問:“我是那種一旦要做這件事,就必須達至他們要求的底線,呈現出的結果也無法高於那個底線,但這事做完就過去了。我已經制成了,要開始想別的(影片工程項目)了。”
締造了“中國速率”攝製奇蹟的《金刚川》
張一白在《我和我的祖国》公益活動現場
本站關於電影海報,預告,影評,新聞,評論的綜合性電影網站,我們提供最新最好的的電影以及在線影評,業務合作亦或意見建議請電郵我們。(Copyright © 2017 - 2022 KKTM)。聯絡我們